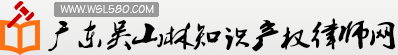真实案例
更多>>在线咨询
一则案例看商标权利人对商标犯罪行为人后期索赔问题 广州资深律师广州打假律师
商标不仅是企业的名片,还是一个企业精神的体现,是对企业文化、企业历史的传承,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驰名商标有时甚至意味着企业的生命。然而,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立法较晚,从而导致对商标权人合法商标权的保护不够全面及完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造假傍名牌等现象愈演愈烈,所以如何有效保护商标专用权,促进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维护企业的信誉,以保证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笔者(广州资深律师广州打假律师)作为有多年商标维权打假经验的专业律师,在最近一起商标权人委托代理其向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中,笔者碰见一些问题,很直观的表现出了我国在商标立法领域以及司法领域的薄弱环节,以下笔者结合实际经验和案例作出论证。
基本案情:原告某公司经营的某品牌系列葡萄酒行销海内外,是中国葡萄酒企业的龙头,拥有多个著名、驰名商标,2012年广东某市公安机关针对该市制假贩假行为展开严厉打击,在该地区查获了大量被告所销售的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并拘留了被告黄某,随后黄某被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余万。随后该企业委托笔者提起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20万元并登报道歉。
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15000元,一个苍白无力的赔偿数额,相对于被告被查获的30多万元货值的假冒原告商标的侵权产品来说,这15000元的赔偿数额,连商标权人为制止侵权而付出的成本也无法弥补,谈何而来的侵权赔偿呢?而法院对于15000元赔偿额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实际证据证明被告有销售产品,所以无法证明原告有获利被告有损失,所以该部分赔偿无法支持只能酌情补偿原告的合理开支15000元。对于以上案情及法院判决,笔者结合实际经验作出以下分析。
一、未销售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1、我国《商标法》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根据该规定,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并不以销售侵权商品为必要条件,即使被告实际上销售未遂,也同样构成侵权。
根据《商标法》第56条第3款之规定,销售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仅限于: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且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既然一审法院也认定了被告人侵权的事实,而被告人又无善意侵权的免责事由,那么就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二、被告犯罪未遂并不代表从未销售过侵权产品。
1、未遂是指已经着手犯罪,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绝对不代表没有开始实施。根据证据被告刑事判决书可知,被告人实际上于2006年8月9日就开始租赁仓库存放酒,2011年8月开始经营“xxx商行”进行酒类销售。刑事判决中所指的未遂仅指库存的那批红酒尚未销售完毕,即相对于被告欲销售的数量来说,可能实际上销售数量不多,且刑法的原则是“疑罪从无”,公安机关只是没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侵权人销售了侵权产品,因此才认定为未遂。被告人被判未遂绝不是指被告从未销售过假冒红酒,事实上被告人进行酒类销售已数年,不可能从未销售,这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没有销售侵权产品的事实没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支撑。
三、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人未实际销售并不代表原告无损失,更不代表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根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认为“鉴于本案涉案侵权产品并未实际销售,原告并无损失,被告也未获利,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1、该判决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没有销售不表示无损失
一审法院的逻辑推断过程是由未实际销售侵权产品从而推论出原告并无损失。这个推论是不合理的。未实际销售侵权产品只是代表销售未遂,并不代表没有危害性,原告的品牌价值无形中受到了威胁和损害,特别是对于原告这种知名度高,驰名中外的品牌来说,又怎能说上诉人没有任何损失呢?一审法院割裂了“未遂”与“危害”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未遂就代表没有危害,只有实际销售了侵权产品,能看得见的损失才称之为损失,而无形的声誉损失、市场份额被挤压等难以举证却显然易见的事实则被忽略不计。这明显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没有实际销售最多只能说明造成的损害小于销售了侵权产品,并不必然推论出没有销售就无损害、无损失。
2、存在法律条文理解错误,无证据证明具体损失数额或侵权所得利益应适用法定赔偿原则,而非不赔偿。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难以取得充分的证据以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的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被侵权人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也即此款规定实际是在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和侵权人在侵权期间的获利均不能查清的情况下所采用的赔偿方式,可以说是一条“救济条款”。换言之,就算无法确定原告所受损失或被被告所获利益,只要有侵权而无免责事由,法院也应根据情节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必须由当事人举证其所受的损失。一审法院在对法条的理解上明显出现错误,错误地认为被告应举证其所受的损失或被告的获利,否则无法得到赔偿支持,这显然与《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相违背。
3、赔偿数额的确定过于片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只片面的考虑到侵权行为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却没有综合考虑商标的声誉、侵权产品的数量及持续时间等其他因素。且实际上本案的合理开支也绝不限于律师费,还应包括在调查阶段需派人去各市场蹲点视察而产生的支付给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的打假费用、查询工商档案费用、报案费用、调查其他相关证据所产生的费用等等。一审法院对赔偿数额的确定过于片面。
4、合理的维权成本不等同于赔偿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合理的维权成本应另行计赔。也即法院在确定赔偿额时应分两部分单独考虑,一是所受损失,二是维权成本,两者综合考虑后再确定赔偿额。不能仅以部分维权成本就确定赔偿额,维权成本并不等同于所受的损失,两者是独立并存的。因此,法院还需根据本案原告的具体损失酌情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完全以律师费代替原告的全部损失。
综上,笔者认为,法院判决的赔偿额过低与商标法的根本精神是互相违背的,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是树立规范更全面地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利,从而打击侵权者的气焰提高侵权者侵权成本杜绝商标侵权行为,而一审法院的判决从某程度上却可能鼓励了商标侵权者的侵权侥幸心理,降低了商标权人维权的积极性。广州资深律师广州打假律师
上一篇:2013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广州知名律师、广州商标维权律师)
下一篇:最后一页